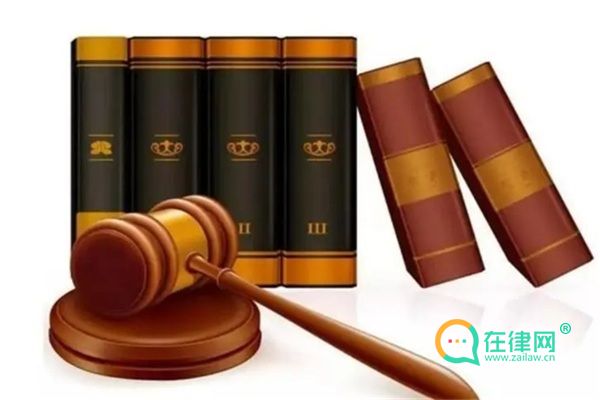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认定掩饰、隐瞒方法的认定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与职务犯罪和其他财产犯罪有密切关系的下游犯罪,职务犯罪和其他财产犯罪实施者在通过犯罪手段获取财产利益后,通常都会通过某种方式将获得的财产在形式上合法化,这一过程往往需要他人的参与,这样参与者的行为可能就会涉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按照刑法规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实施方法分为五种,以下是这五种方法的具体认定标准。

一、“窝藏”及“转移”的认定
何谓“窝藏”?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窝藏是指接受上游犯罪行为人的委托藏匿和保管犯罪所得,使司法机关不能或难以发现犯罪所得的行为。开始不知道是犯罪所得而加以受领,后来在保管过程中知道了是犯罪所得,却继续为保管的行为,也是窝藏。窝藏是一种典型的隐瞒,是以作为的方式来实现对犯罪所得的隐瞒,单纯的知情不举不能认定为窝藏。举例而言,张某盗窃财物价值1万元,藏于家中,张某的父亲事后得知张某盗窃犯罪。后公安机关询问张某的父亲是否知道此事,张某的父亲称不知情,未见到张某盗窃的财物。张某的父亲隐瞒了张某的犯罪所得藏于家中的事实,仅仅属于知情而不举,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何谓“转移”?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转移是指改变赃物存放地的行为。从空间位置上看,转移赃物包括从上游犯罪既遂后的隐藏地向窝赃地的转移以及从一个窝赃地向另一个窝赃地的转移。行为人可以自己转移,也可以同上游犯罪行为人一起转移,还可以通过指挥毫不知情的第三人搬运、转移。对行为人而言,不论其转移赃物是否有偿,转移的距离远近如何,以及行为人在转移过程中是否紧随赃物,这些因素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在同一房间内转移,也可能因妨害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而属于本罪所指的转移,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行为妨害司法的本质,而不是物理上的距离间隔。
二、“收购”及“代为销售”的认定
“收购”和“代为销售”是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所列举的五种行为方式中的两种。如何准确理解本罪的“收购”和“代为销售”,在实践中有一定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1102号陈某、欧阳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对此进行了阐释。
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案裁判理由中指出: “收”和“购”两个字之间是语义的重复,解释为“购买”就可以了。同时也无须对“收购”附加“销售营利”的目的,单纯为了自用而收购的,也是掩饰、隐瞒行为。“收购”的行为类型中包含着“先购后卖”这种情况,根据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立法旨意,法律在这时惩罚的侧重点仍在于“购”,因为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而仍然购买,不管其目的是不是再次出售,购买行为都体现出行为人为上游犯罪人掩饰、隐瞒的主观故意,可能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这是本罪打击的重点。后面再出售的行为就只是实现其个人利益而已,所以刑法条文在这里没有列举“销售”一项,而是在“收购”之后列举了“代为销售”。3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认为:“收购的形式主要是买卖,但也不局限于买卖,只要是提供代价而取得即可,民法上的债务清偿、抵消等都可以构成实质上的收购。仅仅成立了购买的契约还不够,需要现实地进行了赃物的接受,才是收购赃物行为。反之,只要现实地接受了赃物,只是尚未支付对价,或者还没有决定赃物的具体数量和价格,也不妨碍本罪的成立。收购赃物的成立不以行为人从上游犯罪行为人那里直接购买取得为必需,明知是赃物而从其他人处接受转卖的,也是收购赃物。”
所谓“代为销售”,是指行为人代犯罪分子出售犯罪所得的行为。“代为销售”与“收购”不同,它是替犯罪分子销售犯罪所得,中间过程中并没有以自有资金取得对犯罪所得的所有权。“代为销售”既可以表现为行为人以卖主身份替上游犯罪人销售犯罪所得的行为;也包括在犯罪分子与购赃人之间进行斡旋介绍的行为。行为人先将犯罪所得进行窝藏,然后以卖主身份寻找买赃人售出的行为,仍是一种代为销售行为。根据以上分析,本案中被告人陈某、欧阳某的行为属于“先购后卖”,应当解释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收购”而非“代为销售”。
三、掩饰、隐瞒的“其他方法”的认定
根据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条的规定,掩饰、隐瞒的“其他方法”包括: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采取如居间介绍买卖,收受,持有,使用,加工,提供资金账户,协助将财物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协助将资金转移、汇往境外等。(来源于“刑事实务”微信公众号)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第1111号李涛、曹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中的两被告人用非法收购的原油炼制土柴油,属于“其他方法”中的加工。
除此之外,在实际生活中,还可能存在其他应当被认定为“其他方法”的情形。但必须坚持以下三点:“一是行为人的目的是掩饰、隐瞒上游犯罪人的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二是这些方法与窝藏、转移、收购和代为销售在罪质上具有相当性;三是这些方法在客观上扰乱了司法秩序,妨害了司法机关对上游犯罪行为的追究。”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1110号陈飞、刘波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第1112号张晗、方建策、傅鹰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和第1113号吴某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还提及了另外3种被认定为掩饰、隐瞒的“其他方法”的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案的裁判理由中指出:本案被告人傅鹰为张晗、方建策更换被盗电动车锁的行为应认定为“其他方法”。理由是:其一,傅鹰明知是盗窃犯罪所得的车辆仍帮其更换车锁,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掩饰、隐瞒上游犯罪人的犯罪所得;其二,傅鹰更换被盗电动车锁的行为是张晗、方建策销赃过程的重要一环,更换了车锁即掩盖了电动车系盗窃所得的真相,才可能将电动车转卖给他人,因此换锁行为与刑法所列举的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等行为在罪质上具有相当性,与《解释》所列举的“加工”行为更是具有同质性;其三,傅鹰的行为严重妨害了公安、司法机关的追诉活动,助长了他人继续实施盗窃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案的裁判理由中指出:拆解虽然不是《解释》所直接列举的“其他方法”,但是与刑法规定的窝藏、转移、收购和代为销售在罪质上具有相当性,即都是为了扰乱司法机关的追诉活动,便于上游犯罪分子转移、销售赃物,应当认定为掩饰、隐瞒的“其他方法”。这样认定也与已经出台的《机动车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相符。(笔者注:两高2007年《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明知是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的机动车,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二)拆解、拼装或者组装的。)
最高人民法院在马帮勇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中还将“故意毁坏财物”认定为本处的“其他方法”。

 手机扫码,了解更方便
手机扫码,了解更方便